全球動蕩一周:量化寬松“后遺癥”爆發
時間:2016-02-15 15:09:00來源:未知 點擊:0
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全球市場經歷了一場中國“缺席”的集體大震蕩,全球股市可謂“哀鴻遍野”。而避險資產黃金��、歐元�、日元����、歐美債券等價格大漲��。
自2月8日以來,美國股指跌幅一度接近3%����,日本����、法國、韓國股指持續下跌超過11%�����、4.9%�、4.3%�,韓國創業板科斯達克指數觸發8%的熔斷機制�����,恒生指數刷新3年低位����。
這次全球大跌的原因是什么��?是2008年危機的延續還是新危機的卷土重來���?是短暫的陣痛還是長期衰退的開始��?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次巨震引發“雷曼式風險”的可能性不大�,但應對2008年危機的量化寬松后遺癥將逐漸爆發,全球增長模式面臨全面轉型��。
德意志銀行
老牌投行引發的悲劇
德意志銀行是歐洲重要的老牌投行��,近期卻發出危險信號�,成為引發此次震蕩的導火索。
德銀近期公布的四季度財報顯示,該行2015年凈虧68億歐元��,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年度虧損���。雪上加霜的是����,更有消息傳出�,德銀有比德國GDP大20倍的巨大衍生品敞口,德銀2017年或許難以向投資者償付其額外一級資本債券(也稱為CoCo債券)的票息��。負面消息的迅速傳播導致市場恐慌拋售�,德銀或成“雷曼第二”的傳言四散。
自開年以來�,德銀股價已經跌去40%。德銀并非個例�,年初至今的短短1個半月內,歐洲主要商業銀行股價普遍下跌20%~40%����,歐洲銀行較多地將貸款資產配置于油氣開采和與大宗價格有關的行業領域,加之資本充足率保障程度相對較弱�����,令歐洲銀行資產質量堪憂。
在國際頂級投行領域具有20年從業經驗�����、現任玄武智慧總經理李健豪表示�����,與一般可轉債不同�,CoCo債券的派息是按照銀行的還利息能力��、具延遲性和積累性的債券��,所以CoCo債券沒有可轉債的下行保障����。
“之所以說德銀的風險被夸大,是因為CoCo債券的利息如其定義�,本來就可以延遲和積累,而且德銀也有不同手段來融資�����。”李健豪稱���,CoCo債券到期時�����,投資者最后沒有選擇而被必須按照發行時的溢價轉換股票�����,所以沒有任何債務優先的權利��。
盡管當前風險可控��,但彭博也指出�,CoCo債面世僅三年時間,尚未經受過考驗���。鑒于銀行孱弱的盈利能力和市場劇烈波動�,投資者對CoCo債有三重擔憂:銀行可能被迫停止支付債券利息;銀行不會像預期那樣早回購債券���;當然最令人恐懼的是債券本金可能遭受損失����。
“雷曼第二”或被夸大
貝塔基金創始人���、原某海外宏觀對沖基金投研總監郭濤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德銀成為“雷曼第二”可能言過其實。“在兩種情況下高杠桿可能導致損失被無限放大——第一��,黑天鵝事件;第二�����,流動性喪失�。雷曼破產就在于此��。當前歐洲央行仍在推行QE��,并未排除3月擴大QE的可能性��,”他表示��,CoCo債券有強制轉股條款��,乃危機后產物��,為的就是避免雷曼式破產�����,“當債都變成股后,又何談破產?”
“如果德銀繼續下挫�,可能也不失為買入的好時機,因為負面消息基本已經釋放完畢�。”李健豪對記者表示。
其實自去年以來����,每當脆弱的市場聽到一絲風吹草動,諸如“97年亞洲金融風暴卷土重來”����、“2008年金融危機再現”等形容便層出不窮?��!兜谝回斀浫請蟆凡稍L向多位資深業內人士后發現��,各界都認為��,德銀引發“雷曼式風險”的可能性不大��。
接近德銀投行部的人士對記者表示�,德銀的確在前期耗費了大量結構重組成本�,包括2015年的10億歐元罰款�,其也預備支付近80億歐元的訴訟費用�。在負面消息集中反應過后,德銀將會不斷復蘇���,無礙正常運營�。
除了內部努力�����,外部環境似乎尚不具備危機特征��。郭濤告訴本報記者��,危機的傳導鏈通常如下:1)某種危機需要持續發酵�,并形成一致預期;2)投資者產生恐慌���,并對負面消息放大反應;3)恐慌情緒的負反饋導致交易對手集中拋售手中資產;4)去杠桿進行中;5)流動性出現問題����,拆借利率上漲;6)沒有最終貸款人兜底;7)股價大幅下跌;8)再融資失敗���,最終破產;9)評級機構(晚半拍)下調評級�����。
“現在頂多發酵到第二步�,歐洲央行可能會通過QE進一步增加對國債或機構債的購買力度,可見仍存兜底方����。要知道,只要資產可以抵押��、獲取現金流����,就不存在市場自我實現導致抵押品越賣越低的可能,即使發生����,也是緩慢的過程,而投行在此期間完全可以再融資�����,風險緩慢釋放就不構成危機�����,因為銀行的其他業務產生的利率會逐漸彌補虧損。”郭濤對記者稱�����。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德銀當前的杠桿約25倍,要比摩根��、富國(9-11倍之間)等同級別大行的高出一倍�����,確有一定風險��,但危機也需要各種因素集體發酵才會爆發�。
各種增長模式走到盡頭
德銀的“雷曼式風險”只是此輪全球巨震的一環,寬松政策無助經濟增長���、油價暴跌滋生不確定性、美聯儲主席耶倫在國會聽證會上偏鴿派的證詞等���,都加劇了市場悲觀情緒����。
2月10日,耶倫在眾議院發表半年度貨幣政策證詞���,對美國及全球經濟擔憂加重����,貨幣政策鴿派程度不及市場預期��,被市場解讀為美聯儲2016年不會再次加息或加息進程減慢��。
這些只是全球動蕩的催化劑�����,在國泰君安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看來���,這次全球股市大跌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到現在���,歐美牛市太長,浮盈太多����,基本面接不過去����。各種增長模式相繼走到盡頭�,是這次大崩跌的本質。
任澤平認為����,長期看,全球增長前景暗淡�����,人口紅利和追趕紅利等逐漸消失�,貨幣寬松效果邊際下降,各種增長模式相繼走到極致����,發展中國家的粗放式投資增長模式走到極致,美歐日則把貨幣寬松模式走到極致����,這導致全球火車頭相繼熄火。
同時���,全球面臨嚴峻的結構性矛盾����,但各國不愿意直面“現實”�,2008年以來,美歐日無一不是貨幣放水����,缺少結構性改革。長期的低利率和貨幣寬松環境����,鼓勵了過度投機和資產價格泡沫,8年來全球已經積累了過度杠桿�,推高資產價格泡沫,最終要回歸到經濟基本面�����。盡管最近一段時間��,歐洲和日本都先后表示會加大“量化寬松”�,但市場已經對此出現審美疲勞,不再相信通過“放水”就能解決經濟問題�。
全球進入“波動時代”
很顯然,全球經濟已走到新十字路口�,在減少貨幣依賴的同時�,又面臨結構性改革的壓力���,這種轉型���,必將使全球市場進入大波動時代。
“美國標普500指數去年最高的波動幅度是5個標準差的移動��,這是什么概念?當市場出現一個移動就開始波動�,2個就是巨大的波動,而5個移動是1929年以來的最大波動���。”IMF副總裁朱民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
在朱民看來��,當全球進入加息周期��,而經濟增速無法跟上加息的步伐��,市場便會面臨價值重估�。此外,全球經濟的關系愈發緊密�,溢出效應越來越強��,任何地方的小波動都會引發全球波動���,這是今天市場與10~15年前的不同點�。
此外,國際油價仍在30美元/桶徘徊���,暴跌盡管對于如美國這樣的原油進口國是利好�,但對大規模發行高收益債券的美國能源企業仍存隱憂����。前有德銀“雷曼第二”的擔憂,后又有高收益債券“次貸危機第二”的恐慌��。
不過��,牛津經濟研究所美國首席經濟學家Gregory Daco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原油和房貸的本質區別����,還有幾大因素都可以論證,當前高收益債市與次貸危機大相徑庭�����。首先,當前高收益債券多數由無杠桿的投資者持有�,風險蔓延的可能性較小;第二,高收益債券的規模與流通公司債總規模相比小得多�����,也比2007年的住房抵押貸款規模小得多;第三����,在次貸危機時,對資產負債表造成致命性打擊的結構化產品當前并不存在于美國高收益債市��。
值得深思的是�����,就算大危機不會到來����,但面對市場頻繁出現的大幅波動,這對政府�、企業、個人在應對方面都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上一篇:亞太十二國簽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下一篇:2016年中國出口貿易形勢的喜與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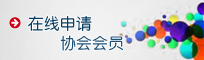
 sitemap 模具網 外貿網站建設 技術支持
sitemap 模具網 外貿網站建設 技術支持